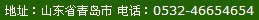|
广西白癜风微信交流群 http://liangssw.com/bozhu/12962.html 1引言 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其古城及大型礼仪建筑群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宝墩文化是文明孕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地区文明起源的中心[1]。众所周知,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古代文明形成的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无疑,积极探索成都平原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对正确认识长江上游地区史前文化的经济基础以及文明化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成都平原史前农业考古的研究还停留在初期阶段,仅有依据古代文献、出土农具、环境变迁以及文化传播等方面的笼统探讨,基本观点认为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可能以粟作农业为主[2-4]。要最终揭示出该地区史前农业起源及其形态等问题还需要更多直接的、明确的植物遗存证据。 ▲宝墩遗址 如今,成都平原地区的浮选工作已经陆续展开。宝墩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初步大植物遗存研究结果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该地区有可能已确立了稻作农业为主,粟作农业为辅的经济形态,并且一直持续到商周时期[5-6]。然而,由于四川盆地的植物考古工作起步较晚,仍处于基础资料的积累阶段。同时可能由于当地的土壤黏度高,导致炭化大植物遗存保存较差,从而严重影响了相关史前农业信息的提取[5]。与之相比,植硅体理化性质稳定,具有原地沉积性、高残留性以及种属形态差异性等优点[7],可有效验证和补充大植物遗存的分析,更加全面地揭示先民利用植物的信息。尽管如此,较之长江中下游等地区[8-12],植硅体分析在四川地区农业考古中的应用较少,目前仅有都江堰芒城遗址的灰坑[13-14]及汉源麦坪遗址的文化层和灰坑开展过植硅体分析[15]。 ▲航模拍摄宝墩遗址发掘全景照片 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文明起源最古老、最重要的文化之一。宝墩遗址(-BP)是宝墩文化时期最为重要的古城址。本文拟从成都宝墩遗址的代表性剖面和两处灰坑选取样品,进行植硅体分析,结合浮选结果,以期更深入地揭示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时期农业生产状况,为探索成都平原早期文明的兴起提供新的资料和线索。 2遗址背景 宝墩遗址位于新津县城西北约5km的龙马乡宝墩村,地理位置为东经°45′、北纬30°26′,海拔高度-m。遗址东北距发源于崇州市的西河约4km,西南m处有铁溪河由西北流向东南[16](图1)。研究区位于成都市区西南38km,处在川西平原西南边缘,与川西南低山丘陵接壤。该区地势平坦,属亚热带湿润气候亚区,四季分明,多年平均气温为15~16℃,多年平均降水量约mm[17]。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中,宝墩遗址的面积最大、年代亦最早。最新的考古调查显示,宝墩遗址外城墙所包含的范围达2.76平方千米,是目前发现面积最大、且具有内、外双重城墙的龙山时代城址之一[18]。宝墩遗址的城垣周长近6.2km,宽15-25m以上,高度超过4m。该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有较精致的斧、锛、凿、穿孔石刀等磨制石器以及陶质的纺轮和网坠等。生活用器主要是陶器,其泥质陶多于夹砂陶,盛行小平底器和圈足器。典型器物有绳纹花边罐、喇叭口高领罐、圈足尊等。房屋多为小型的木骨泥墙建筑,表面有火烘烤过的痕迹。上述发现表明,宝墩先民已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19]。 ▲图1宝墩遗址地理位置示意 Fig.1SketchmapshowingthegeographiclocationoftheBaodunsite 3样品的采集 年10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墩遗址田角林东北区域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平方米。以常规的柱状采样法从宝墩遗址T西壁剖面选取了8个样品(图2),同时运用水平采样法从属于宝墩文化一期灰坑H92和H94选取了2个样品。现将T西壁剖面的文化内涵介绍如下: 第1层,灰黑色耕土,土质疏松,厚20-22cm。 第2层,灰褐色黏土,土质较致密,厚23-26cm,有少量青瓷、白瓷出土,为唐宋时期堆积。 第3层,浅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厚15-17cm,有少量泥质灰陶出土,主要器类为釉罐和板瓦,其中夹杂少量宝墩文化时期陶片,为汉代堆积。 第4层,黄褐色黏沙土,土质疏松,厚10-11cm,有少量石块、红烧土和褐泥质灰陶出土,主要器类有罐和板瓦,其中夹杂少量宝墩文化时期陶片,同为汉代堆积。 第5层,青灰色黏沙土,土质较致密,厚20-22cm,可分为3个亚层。包含物与第4层基本一致,亦为汉代堆积。 第6层,灰色黏土夹杂大量褐斑,土质致密,厚14-16cm,包含物有少量石块、红烧土、炭屑和陶片,可辨器类有喇叭口高领罐、宽沿平底尊、敞口圈足尊、盘口圈足尊等,为宝墩文化二期的堆积。 第7层,黑褐色黏土,土质较致密,厚22-24cm,包含物与6层基本一致,为宝墩文化一期的堆积。 第8层为生土。 根据年的发掘简报和最新的测年结果,将宝墩文化分为四期,其年代范围大致推定在距今~年之间,每期延续时间两、三百年[19-20](图3)。 ▲图2宝墩遗址T西壁采样示意图 Fig.2SketchmapshowingthesamplinglocationoftrenchTattheBaodunsite ▲图3宝墩遗址C14年代数据 Fig.3C14datingdatafromtheBaodunsite 4实验方法 采用赵志军改进的重液浮选法[21],对样品进行处理。具体步骤简述如下:首先,将土壤样品溶于6%碳酸氢钠溶液,震荡分散8~12小时;然后依次加入稀盐酸、浓硝酸和双氧水,以去除碳酸盐和有机物等;接着采用重力沉降法去除黏土,并将样品过60目网筛;再以比重为2.3~2.4的碘化钾与碘化镉重液,浮选出样品中的植硅体,清洗后,用加拿大树胶制片。将制成的样品置于日本Nikon公司生产的型号为eclipseLVP0L的显微镜(×和×)下进行观察、鉴定,并作数量统计。每一个样品均随机选择了粒左右的植硅体进行统计分析。按照最新的国际植硅体命名法规(Internationalcodeforphytolithnomenclature1.0)对部分植硅体的描述和命名做了更新[22],同时列出传统命名以资对照。 5结果 宝墩遗址剖面和灰坑样品中,植硅体的基本组合为长方型、方型、扇型、双裂片型(哑铃型)、长鞍型、短鞍型、棒型、刺棒型、帽型、针型毛细胞(尖型)、波状梯型(齿型)等,此外还有海绵骨针和硅藻等生物化石(图4和5)。根据植硅体主要类型数量的变化,可将植硅体图谱自下而上划分为5个组合带(图6)。 带Ⅰ(生土层):植硅体组合以扇型、方型、长方型、棒形等为主,其次是芦苇扇型、双裂片型(哑铃型)和针型毛细胞(尖型),并含有少量鞍型、波状梯型(齿型)、帽型以及硅藻和海绵骨针。一定量的芦苇扇型和硅藻、海绵骨针的发现,反映了当时该区域为潮湿的水环境。 带Ⅱ(新石器时代晚期,对应⑥~⑦层):植硅体组合仍是以扇型、方型、长方型、双裂片型(哑铃型)为主,鞍型和帽型有少量增加,芦苇扇型和棒形减少,海绵骨针消失。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水稻扇型、横排双裂片型(哑铃型)和双峰型植硅体以及黍稃壳植硅体。 带Ⅲ(汉代时期,对应③~⑤层):机动细胞植硅体扇型、方型和长方型总的比例增加,占组合中的绝大多数。双裂片型(哑铃型)和帽型减少,农作物仅见少量水稻扇型植硅体,基本不见海绵骨针和硅藻。 带Ⅳ(唐宋时期,对应②层):植硅体组合仍以扇型、方型、长方型占绝大多数,双裂片型(哑铃型)型消失,基本不见海绵骨针、硅藻和农作物植硅体。 带Ⅴ(耕土层,对应①层):扇型、方型、长方型植硅体有所减少,但仍占大多数。双裂片型(哑铃型)、鞍型、帽型、波状梯型(齿型)和棒型增加,一度消失的海绵骨针、硅藻和水稻植硅体再次出现。 图中标尺棒长均为20μm(Scalebar=20μm) (a)T⑥层长方型植硅体(Rectangle);(b)T⑥层方型植硅体(Square); (c)T⑦层扇型植硅体(Cuneiformbulliformcell);(d)T⑦层芦苇扇型植硅体(Scutiform);(e)T⑥层双裂片型植硅体(Bilobateshortcell);(f)灰坑H92竹节型植硅体(Oblongconcavesaddle);(g)灰坑H94刺棒型植硅体(Elongatesinuous);(h)T⑦层棒型植硅体(Elongate);(i)T⑥层针型毛细胞植硅体(Acicularhaircell);(j)T⑥层波状梯型植硅体(Trapeziformsinuate);(k)灰坑H94硅(Diatom);(l)T⑥层海绵骨针(Spongespicule);(m)T⑥层水稻扇型植硅体(Cuneiformbulliformcellfromrice);(n)灰坑H94水稻双峰型植硅体(Double-peakedglumecell);(o)T⑥层水稻横排双裂片型植硅体(Parallel-bilobateshortcell);(p)T⑥层黍稃壳η型植硅体(η-shapedhuskphytolithfrommillet) ▲图4墩遗址T主要植硅体形态和硅藻化石 Fig.4PhotographsofrepresentativephytolithsanddiatomsfromtrenchTattheBaodunsite ▲图5宝墩遗址H92和H94植硅体、硅藻百分含量图谱 Fig.5Contentchange(%)ofphytolithsanddiatomsfrompitsH92andH94attheBaodunsite ▲图6宝墩遗址H92和H94植硅体、硅藻百分含量图谱 Fig.6Contentchange(%)ofphytolithsanddiatomsfromtrenchTattheBaodunsite 6讨论与结论 农业是文明产生的深厚基础。关于成都平原史前农业经济形态探讨,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非常关心的热点问题。很多学者基于古代文献记载、出土农具、环境变迁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初步的探讨,认为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可能以粟作农业为主[2-4]。成都宝墩遗址的植硅体分析指出,宝墩文化层和灰坑样品中发现了大量产生于水稻叶秆的驯化特征扇型植硅体(底侧面布满龟裂纹,两侧向外突出)以及横排双裂片型(哑铃型)和产生于水稻颖片的双峰型植硅体。此外,还发现少量的粟类作物黍稃壳植硅体(图4和5)(可能也有粟稃壳植硅体,因破碎严重,无法确定)。有学者指出,若某一考古遗址的同一遗迹中出现不同类型的水稻植硅体和大植物遗存,那么基本可确定该遗址曾存在栽培稻[23]。这次在宝墩遗址的宝墩文化地层和灰坑中,既然发现都有典型扇型,横排双裂片型(哑铃型)和双峰型等多种类型的水稻植硅体,那么这些水稻遗存很可能属于栽培稻。值得指出的是,宝墩文化层和灰坑中,所发现的水稻扇型植硅体大多呈典型的驯化形态,即扇型边缘呈“鱼鳞状”纹饰的数量大于9个[24](图4m),从而进一步证明宝墩遗址发现的水稻植硅体来自栽培稻。此外,9年宝墩遗址的浮选结果,也显示无论是宝墩文化一期阶段,还是到了汉代,该地区都是以水稻的种植为主,粟仅在宝墩文化一期占有少量比例[5]。由此可见,植硅体的分析结果与浮选分析结果基本吻合。 将从宝墩遗址T的第6层和第7层以及属于宝墩文化一期的两个灰坑H92和H94中获得的水稻扇型植硅体进行了形态测量分析。结果发现,这批水稻扇型植硅体形态的总体尺寸较大。从表1可以看到,属于宝墩文化一期的水稻扇型植硅体的形状系数平均值是0.98,二期为0.99,它们都处于粳稻范围内[25]。同时,炭化稻米的形态测量结果,长宽比平均值为1..3,同样符合粳稻特征[26]。综合上述两方面的分析,可以推测宝墩先民以种植粳稻为主。另外,将宝墩遗址水稻扇型植硅体形态测量的数据与来自太湖地区几个遗址的相关数据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宝墩遗址水稻扇型植硅体的尺寸明显偏大[27]。这一现象是否在成都平原地区具有普遍性,如何认识其产生的机制和原因,目前尚无同类的材料可供对比分析,有待今后作更深入的探讨。 表1宝墩遗址与太湖地区部分新石器时代遗址水稻特征扇型植硅体形态参数对比数据 Tab.1MorphologicalparametersdataofricecuneiformbulliformcellphytolithfromtheBaodunsiteandsomeNeolithicsitesinTaiLakearea 综上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1)宝墩遗址的植硅体分析表明,该地区的土壤环境能够较好地保存古代植硅体记录,为研究古代农业和环境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手段,也为以后在该地区开展类似的工作奠定了基础。2)宝墩文化一、二期先民的经济形态是以稻作农业为主,所栽培的稻种可能属于粳稻类型,同时兼有粟作农业。稻作农业的发展,为成都平原早期文明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致谢:感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石涛在取样期间给予的帮助。 参考文献: [1]段渝,陈剑.成都平原史前古城性质初探[J].天府新论,1(6):81-86 [2]郭声波.巴蜀先民的分布与农业的起源[J].四川文物,(3):23-27 [3]霍巍.成都平原史前农业考古新发现及其启示[J].中华文化论坛,9(增刊2):- [4]孙华.四川盆地史前谷物种类的演变——主要来自考古学文化交互作用方面的信息[J].中华文化论坛,9(增刊2):- [5]姜铭,玳玉,何锟宇,等.新津宝墩遗址9年度考古试掘浮选结果分析简报[A].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编.成都考古发现(9)[C].北京:科学出版社,:68-82 [6]姜铭,赵德云,黄伟,等.四川成都城乡一体化工程金牛区5号C地点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分析报告[J].南方文物,(3):68-72 [7]PipernoDR.Phytolith:AComprehensiveGuideforArchaeologistsandPaleoecologists[M].NewYork:AltaMiraPress,6 [8]张玉兰,张敏斌,宋建.从广富林遗址中的植硅体组合特征看先民农耕发展[J].科学通报,3,48(1):96-99 [9]萧家仪,徐时强,肖霞云,等.南京郭家山遗址植硅体分析与湖熟文化环境背景[J].古生物学报,,50(2):- [10]LiRC,CarterJA,XieSC,etal.PhytolithsandmicrocharcoalatJinluojiaarchaeologicalsiteinmiddlereachesofYangtzeRiverindicativeofpaleoclimateandhumanactivityduringthelast0years[J].JournalofArchaeologicalScience,,37:- [11]ZhaoZJ.ThemiddleYangtzeregioninChinaisoneplacewherericewasdomesticated:PhytolithevidencefromtheDiaotonghuanCave,northernJiangxi[J].Antiquity,,72:- [12]姚政权,吴妍,王昌燧,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植硅石分析[J].农业考古,6(4):19-26 [13]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市芒城遗址年度发掘工作简报[A].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编.成都考古发现()[C].北京:科学出版社,1,54-98 [14]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市芒城遗址年度发掘工作简报[A].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编.成都考古发现()[C].北京:科学出版社,1:99- [15]黄翡,郭富,金普军.麦坪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水稻植硅体的发现及其意义[J].四川文物,(6):79-83 [16]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联合大学考古教研室,新津县文管所.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调查与试掘[J].考古,(1):40-52 [17]赵志中,乔彦松,王燕,等.成都平原红土堆积的磁性地层学及古环境纪录[J].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7,37(3):- [18]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县文管所.新津宝墩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9-年)[A].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编.成都考古发现(9)[C].北京:科学出版社,:1-67 [19]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年发掘简报[J].考古,(1):29-50 [20]江章华,颜劲松,李明斌.成都平原的早期古城址群——宝墩文化初论[J].中华文化论坛,(4):8-14 [21]ZhaoZJ,PearsallDM.Experimentsforimprovingphytolithextractionfromsoils[J].JournalofArchaeologicalScience,,25:- [22]李泉,吕厚远,王伟铭.国际植硅体命名法规(InternationalCodeforPhytolithNomenclature1.0)的介绍与讨论[J].古生物学报,9,48(1):- [23]靳桂云,方燕明,王春燕.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土壤样品的植硅体分析[J].中原文物,7(2):93- [24]LuHY,LiuZX,WuNQ,etal.Ricedomesticationandclimaticchange:PhytolithevidencefromEastChina[J].Boreas,2,31:- [25]王永吉,吕厚远.植物硅酸体研究及应用[M].北京:海洋出版社, [26]王象坤,孙传清,才宏伟,等.中国稻作起源与演化[J].科学通报,,43(22):- [27]郑云飞,藤原宏志,游修龄,等.太湖地区部分新石器时代遗址水稻硅酸体形状特征初探[J].中国水稻科学,,13(1):25-30 [基金项目]本课题得到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CB)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1145)资助。 [作者简介]陈涛(-),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植物考古学研究。E-mail:chentaose7en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shuangfengzx.com/sfxzf/14148.html |
当前位置: 双峰县 >四川新津宝墩遗址的植硅体分析
时间:2022/8/30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周末去哪儿记住双峰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