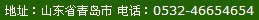|
格奥尔格·齐美尔 (原文发表于《社会学研究》年第4期,本文为专题研究——“理论研究:回思经典”第三篇) 编者按 回思经典社会理论传统,我们认为,理论绝不仅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建构,而总是面对现代社会的实质问题和人心经验。因而,重返经典,不仅是为了重建社会学的理论想象力,也是为了重建社会学的经验感和历史感。作为一个尝试,本期编发三篇论文,对弗洛伊德、滕尼斯、齐美尔等经典社会学家进行研讨,以期推动社会理论研究重返经典、重新挖掘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 摘要 无论人类学的耻感文化研究,还是以舍夫为代表的当代学者对齐美尔、埃利亚斯、戈夫曼等人有关羞耻的思想的社会心理学解释,都忽视了羞耻对于现代“抽象社会”的重要意义。实际上,从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到埃利亚斯的型构社会学和戈夫曼的结构社会学,羞耻背后的核心问题始终是自我与现代“抽象”社会之间的张力。现代社会的“抽象性”及其导致的社会距离、社会利益甚至个体自我的暧昧性,是羞耻产生的结构性根源。因此,羞耻不仅是偏差行为的心理动机和非西方社会的主导情感,而且是理解现代社会与文明进程的关键。 关键词 羞耻;自我;齐美尔;埃利亚斯;戈夫曼 在古希腊社会,表示羞耻的aid?s一词具有很广泛的含义,其中还包括了罪感(威廉斯,:99-)。似乎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罪感与耻感的区分和对立才变得日益显著。20世纪初,弗洛伊德最早指出,耻感主要存在于儿童和野蛮人身上,罪感则是成人和文明人的感受,因而个人成长史和文明史就成为了从耻感到罪感的转变过程(Scheff,)。20世纪中期,这对概念在社会科学中得到诸多运用,最著名的便是本尼迪克特对美日文化差异的比较研究(本尼迪克特,)。这种文化研究似乎暗含着一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日本等落后的非西方社会主要是耻感文化,西方社会则是罪感文化,前者不过是后者的“童年”或“过去”(Creighton,;Ikegami,)。 其实,西方人自身的羞耻并未完全受到忽视。跟耻感文化研究强调非西方与西方之间差异不同的是,齐美尔、埃利亚斯、戈夫曼等人都将羞耻作为切入点来理解西方文明与现代社会。然而,这几位社会学家虽然名声显赫,但其有关羞耻的思想却鲜受重视,甚至不被他们自己所看重。齐美尔只是在《羞耻心理学》这篇短文中直接讨论了羞耻问题,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重点论述的羞耻主题在其后期著作中逐渐消失,戈夫曼主要白癜风医院北京中科医院好不好
|
当前位置: 双峰县 >王佳鹏羞耻自我与现代社会从齐美尔到
时间:2017/10/11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新化人注意这9种行为属于犯罪,稀里糊涂
- 下一篇文章: 衡东这是我的家乡,请不要嫌弃她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