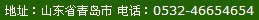|
《韩非子?五蠹》:“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上古之世,工具比较原始,人们能吃到的海物大多是容易捡拾的蛤,在胶东地区发现的几处新石器文化遗址都发现有贝丘和蛤堆,说明我们食用蛤类的历史已经有上万年了,但对于蛤是怎么来的、蛤有哪些种类,古人一直没有搞清楚。 蛤螺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含有蛋白质、维生素和无机盐图/小草 古人识蛤 《说文解字?虫部》:“蛤,蜃属。有三,皆生于海。千岁化为蛤,秦谓之牡厉。又云百岁燕所化。魁蛤,一名复累累,老服翼所化。”这里的概念比较混乱,需要仔细梳理一下。《礼记?月令》:“季秋之月雀入大水为蛤。”《易经?通卦验》:“立冬燕雀入水为蛤。”在古人看来,到了秋冬季节,很多鸟雀都不见了,那时还不知道候鸟一说,古人寻思这些鸟雀去哪里了?可能入水变成蛤了吧。《国语?晋语九》:“雀入于海为蛤,雉入于淮为蜃。”《国语注》:“小曰蛤,大曰蜃。”小雀化为蛤,大鸟化为蜃,蜃,就是大蛤蜊。海市蜃楼是大气中由于光线的折射作用而形成的一种自然现象,蓬莱阁即以海市蜃楼而闻名遐迩,古人误认为这是蜃吐气而成,所以叫蜃景。许慎认为千岁雀化为蛤,百岁燕化为牡厉即牡蛎,老服翼就是老蝙蝠,入水化为魁蛤———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魁蚶。《说文》中的蛤包括蛤、蛎、蚶三个种类,与现代生物学的分类体系存在较大差异。 清代郝懿行《记海错》“蛤”条:“蚌之属,《说文》所谓砺也。壳圆而厚,有文回旋,如指头文,大者如酒杯,作青白色;其类亦有纤如指顶,黄白杂文,壳薄而光,乃文蛤之属,非此也。蛤一名蛤蜊,肉甚清美,热酒冲啖,风味尤佳。宋庐陵王义真车螯下酒(《宋书刘湛传》:‘臑酒炙车螯’),珍可知矣。《大观本草》言车螯是大蛤,一名蜄,即此是也。腹有小蟹,螯足悉具,状如榆荚,是蛤之精,蛤在壳中,不能取食,当其饥虚,蟹辄走出为蛤觅食,蟹饱则蛤饱,晨出暮还,有肉如丝为之牵系,或猝遭风浪,丝断蟹僵,蛤即顿仆,郭璞《江赋》所谓璅蛣腹蟹,当即指此。而璅蛣非蛤,恐同类异名耳。《北齐书徐之才传》:‘有人患脚跟肿痛,诸医莫能识,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实曾如此。”之才为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荚。’即是物也,谓之精者,知觉攸存。至于文蛤之伦,腹中无蟹。” 这段文字中,列举了蛎、文蛤、车螯、蛤蜊四种,仍显混乱。其后半段“蛤精”一节,则颇类笔记小说。吃过海鲜的人都知道,某些贝类壳里会有一种小豆蟹,贝类与豆蟹就跟海蜇和某些虾类的关系一样,古人称为“璅蛣腹蟹,水母目虾”,这在生物学上叫“共生”关系,与精怪无涉,很好奇徐之才是怎样从那人的脚后跟里剖出蛤精的。 郝文中的“蛤蜊”,据专家研究,唐宋之前,从广义上来说为蛤类的通称,包括文蛤、花蛤与西施舌在内的多数蛤类生物,从狭义上说,专指某一蛤蜊,以区别于文蛤与西施舌。从唐宋之后,蛤蜊义渐狭,多指蛤蜊科的蛤类。郝文中将蛤蜊与文蛤并举,显然取其狭义,古人所说的蛤蜊多形容为白壳紫唇,壳呈白色,腹面周缘具有一圈黑紫色边缘,按此形态,所指应为四角蛤蜊,是古人最为看重的一种海蛤,《水产志》 上说山东羊角沟和烟台盛产,但黄县(今龙口)海域好像很少见到这种贝类。《现代汉语词典》释“蛤”:蛤蜊、文蛤等双壳类软体动物。释“蛤蜊”:①软体动物,长约3厘米,壳卵圆形,淡褐色,边缘紫色。生活在浅海底。②文蛤的通称。这里的蛤蜊基本也是取其狭义,而蛤的含义略微宽广一点。 在黄县话中,蛤的内容进一步丰富,除了蛤蜊科的四角蛤蜊、中国蛤蜊(即黄县话中的“黄蛤”),帘蛤科的文蛤、日本镜蛤、菲律宾蛤仔(即黄县话中的“花蛤”)之外,樱蛤科的“海瓜子”(学名为虹光亮樱蛤),等等,都可叫作“蛤”。 而且,不光含义有变化,读音也不相同。“蛤”普通话里读“gé”,“蛤蜊”“蛤蚧”都这样读,在黄县话中,蛤却读作“gá”,黄县话将普通话中的韵母“e”换成“a”并不是个别现象,比如“喝”,黄县话读作“há”,我们往往就着音写成“哈”;比如“割”,黄县话读作“gá”,“割麦儿”“割肉”“手割儿个口儿”,都这样读;比如“搿”,普通话读作“gé”,黄县话读作“gá”,“买卖好做,伙计难搿”“搿邻居”都这么读。黄县话里还把男女相好的称为“搿乎儿”,比如:“他有好几个搿乎儿”。其他的,像“葛”“磕”“瞌”,俱是如此。 在黄县话里,比“蛤”含义更丰富的是“蛤螺”,此处“螺”轻声变韵,“uo”读作“ou”,“波螺”“耳朵”“掂掇”都作如是读。黄县人所说的蛤螺,包括双壳纲中除了贻贝科、扇贝科、牡蛎科、竹蛏科之外(这几科都有专用名称)的大部分的贝类,也就是说,除了上文的蛤包含的种类之外,海水中的砗磲科和蚶科也可以叫蛤螺(比如毛蚶黄县话就叫“毛蛤”),甚至淡水中的蚬科和珠蚌科,都可以称为蛤螺。 记得有一年天大旱,水库见了底,我跑去用脚踩出六七十个河蚌,想看看里面有没有珍珠。当时没有东西盛,只好脱了裤子扎好裤腿,装了一裤子的河蚌扛回家,村里人见了都说:“你抓这些个大蛤螺做什么?”我忙活了半下午,才明白他们的质疑是有道理的,这玩意儿真不能做什么,不用说人吃了,连我家的鸡鸭对其都兴趣缺缺。后来才知道那大蛤螺叫背角无齿蚌,如果没有人工植核,是极少产珍珠的,即便产了质量也较次。 黄县人所说的“蚬儿”,包括中国蛤蜊、菲律宾蛤仔和虹光亮樱蛤等,都属于蛤螺的范畴,我在另一篇文章里谈过,这里不再赘述。 黄县海域还有几种蛤螺,值得一说。一种是文蛤,属于双壳纲帘蛤目帘蛤科贝类,贝壳背缘呈三角形,腹缘呈圆形,贝壳坚厚,表面膨胀、光滑,外被一层光泽油润的黄褐色壳皮,布有花纹,用黄县话说看上去“肉奶奶”的,顶部斑纹常呈锯齿状,所以黄县话称之为“花皮儿”,浪脉(即近岸的几道沙滩,海水涨潮时到此起浪,黄县话称为“浪脉”)上较多,深水里没有。文蛤炖汤最鲜,为蛤中上品,除炖汤外,文蛤蒸蛋也是一道名菜。文蛤的壳可做工艺品,上点年纪的人都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出一款“蛤蜊油”,就是把擦手油装在文蛤壳里,这个创意简直绝了,我们上学时都带着自己的蛤蜊油,互相比一下蛤蜊壳的大小,看谁的花纹更漂亮。 有一种与文蛤同属帘蛤科的日本镜蛤,黄县海域有少量出产,贝壳近圆形,如牛眼,所以又叫“牛眼蛤”。壳坚厚,稍扁平,有一次我下海游泳摸到一只,立在细沙中,入手像摸到一面小圆镜,壳面白色,生长纹宽而粗,无放射肋,打开后壳内面是羊脂玉一般莹润的白色,特别漂亮。 蚶类三兄弟 毛蚶属双壳纲蚶目蚶科贝类,蚶科有个特点就是放射肋凸出,纹理如瓦垄,其壳入药称“瓦楞子”。毛蚶因壳面被有褐色绒毛状表皮而得名,黄县话称为“毛蛤”,壳内面白色,边缘有齿。毛蛤喜欢生活在泥质海滩,河口附近更多,浅海细沙区有零星分布,我曾在游泳时摸到过,咬开生吃腥味很大,味道和黄蛤没法比。 毛蛤的分布面积及资源量在山东省的海洋贝类中均占首位,记得小时候每到秋天,村里小卖部就会拉来一车毛蛤堆在门前,用铁撮子撮了卖,价钱极便宜,几分钱一斤,回家洗净蒸一下,就可以吃了。毛蛤火大了“登艮”,火候以刚开口为好,有些没开口的,要用硬币掰一下壳顶的绞合齿才能打开。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曾因食用被污染的毛蛤造成甲肝大爆发,此后就没怎么吃过毛蛤了。 泥蚶和毛蛤长得很相像,只是没有毛,壳作灰白色,南方比较多,养殖泥蚶的滩涂称为“蚶田”。吃泥蚶时里面一汪红红的汤汁,像是血水一样的,所以又被称为“血蚶”,据说是极有补的。 魁蚶是蚶类三兄弟中个头最大的,《说文》:“魁,羹斗也。”段玉裁注:“《毛诗传》曰‘大斗,长三尺’是也。引申之,凡物大皆曰魁。”大者有拳头大小,黄县人不知其名为魁蚶,呼为“大毛蛤”。它和毛蛤确实长得很像,但比毛蛤要大得多,这从个头上很容易区分,可是如果同样大小的三种蚶放在一起该怎么区分呢?泥蚶没有毛,相对好区分一点,不过最科学的办法还是数它们的放射肋,毛蚶在35条、魁蚶在40条以上,泥蚶最少只有20条左右,所以它的放射肋最粗壮。魁蚶的斧足大而赤红,所以又称“赤贝”,日本料理喜欢用赤贝做刺身或寿司,比蒸煮的味道要鲜美。 还有一种贝类样子和蚶类有点像,也有细密的放射肋,但壳表面是红褐色的,没有毛,生长纹是分层的,如长草苫屋,层层相叠,学名叫鸟蛤,属于双壳纲帘蛤目鸟蛤科,黄县海域有少量出产,我下海摸到过完整的贝壳,但没有捉到过活体。 鸟蛤的得名源于它的细长弯曲的小舌头(斧足),造型像个鸟头,饭店里一般称之为“鸟贝”,它的小舌头多用来蘸辣根生吃,鲜甜脆嫩,入口难忘。还有一种蛤,样子和鸟蛤比较相似,也有放射肋和生长纹,相比鸟蛤,它的放射肋更细密,生长纹的分层不是那么明显,二者纵横交织,状如布纹,所以称为“江户布目蛤”,属于双壳纲帘蛤目帘蛤科,与文蛤、日本镜蛤、菲律宾蛤仔同属一科,据说蓬莱海域产的比较多。 蛤螺种类众多,绝大部分可供食用,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无机盐,对人体极有益处,更难得的是蛤螺价格低廉,是真正平民化的海鲜。夏天的傍晚,炒一盘辣蛤,蒸一盆毛蛤,冰几打啤酒,邀三两好友,聊几句闲天,人生若此,夫复何求? 赞赏 长按向我转账 受苹果公司新规定影响,iOS版的赞赏功能被关闭,可通过转账支持。 白癜风哪个医院看好白癜风医院西宁哪家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shuangfengzx.com/sfxxw/2433.html |
时间:2018/3/25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转诗词韵字新编完整版
- 下一篇文章: 国宝砗磲第一章下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